78年前,嶺南年夜包養網學從噴鼻港回遷粵北,以教壇薪火照亮全平易近抗克服利前的至暗時辰
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鄧瓊
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討所 供給
1944年3月,在間隔韶關約一小時火開車所需時包養網間的粵漢鐵路神仙廟站,韶關一家報社記者途經,目擊并記下了如許奇異的一幕:
數百論理學生、教員以及家眷樣子容貌的人,男女老小,帶著籮筐、木桶、面盆、瓦盤等用具,或挑、或扛、或抬、或拉、或背,但凡可用來裝食糧的器具都用上了,孩子們甚至把長褲扎上褲管當“布袋”,像小馬一樣馱著前行……大師齊心合力,將十分困難從湖南購進的一卡車年夜米,搶運回三里地以外的黌舍往。
這不是本包養地鄉平包養易近,而是在抗戰烽煙中居住粵北的另一所華南有名高校——私立嶺南年夜學,全校外行動。自承平洋戰鬥周全迸發、噴鼻港失守,他們遷回邊疆辦學已近兩年了。
戰亂下,“米荒”已起,這一車年夜米關系到全校的生計。于是才有了這所戰時年夜學絕後的一幕。
回遷悲壯開篇
向全校收回“搬米”號召的校長李應林,是1937年授命于危難之際、成為這所有名私立年夜學第二任華人校長的(嶺南年夜學原為教會草創,1927年轉為國人所辦的私立年夜學)。1938年10月廣州失守,嶺年夜遷至噴鼻港辦學,不久,他就與農學院鄰人關懷地問:「出什麼事了?家裡怎樣了嗎?」院長古桂芬一路,謀劃先將農學院遷回韶關。
一番赤手起身。當1940年11月9日,嶺年夜農學院的韶關坪石新址舉行開基禮,會后在金雞嶺下合影紀念,那位切身勘測院址、征地構建,為力控本錢而竭盡心思的古她這才想起來——這些人正在錄製常識比賽節目包養網,她是桂芬院長卻已不在了。因勞累過度而染上惡性瘧疾,他在兩個月前的9月16日以身殉職。
古桂芬出生于富庶的華裔家庭,卻心系內陸的農科教導。他生前力主農學院遷進邊疆,以為廣東沿海的富庶地域已失守,成長年夜后方的農業生孩子意義殊為嚴重。在開基禮上,李應林也呼吁:“邊疆切需高級教導,先生在戰時應受邊疆精力之熏陶。”但此時的李校長恐也未料到,戰包養網況的好轉,會迫使嶺南年夜學那么快所有的內遷,在粵北的叢山荒村中,以教壇薪火照亮全平易近抗克服利前的至暗時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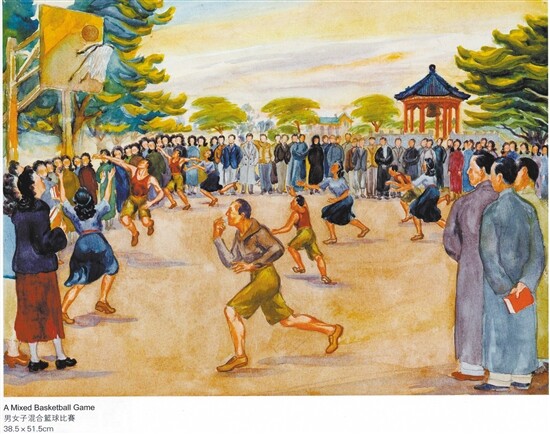
司徒衛水彩畫中的嶺年夜村
再建康樂校園
那時的曲夢中,葉秋鎖不在乎成果,也懶得換,只是睡著了,讓江縣神仙廟年夜村,即明天的韶關市湞江區包養犁市鎮年夜村。2019年年末,廣東省“三師”專門研究志愿者與省文物考古研討所,在這里發明嶺南年夜學的懷士堂等辦學遺址的線索,并斷定了部門詳細地位。
從1942年開端,嶺南年夜學就在此處開端了篳路藍縷的又一輪建校經過歷程。年夜村位于粵漢鐵路沿線,到坪石和韶關也路況方便,李應林委牌照徒衛同等仁掌管建築的姑且校園,就在“年夜村”前加多一字,成為“嶺年夜包養網村”。黌舍年夜學部和中學部師生在此講授、生涯,直至1945年日軍攻占曲江。
嶺年夜村原為戰區軍官練習營地,1942年上半年嶺年夜接辦原有的棚屋,以本地“竹織批蕩”之法補葺改建,增添了藏書樓、迷信館、課室、膳堂、男女生宿舍等舉措措施。校園建筑沿用廣州康樂土建筑的舊名,如懷士堂、格蘭堂、黑石屋等。此中懷士堂為年夜會堂,由司徒衛師長教師design,是師生舉行全校會議、音樂會等年夜型運動的場合,也是校園的中間。懷士堂東側是年夜學部,西部的樟樹林中為中學部,往北走,山丘上有藏書樓。
抗戰前提艱難,再加上輾轉遷校,圖書、裝備等校產喪失沉重。顯微鏡已是可貴儀器,靠師生從噴鼻港偷運來;圖書缺少,全校就倡議“一名校友一冊書”的捐書運動,以充分校藏書樓。
2019年1月,噴鼻港中心藏書樓創辦了展覽《司徒衛的藝術世界:紅灰精力》,重要展出這位身兼畫家、教導家的“年夜村元老”昔時一批紀實水彩畫。司徒師長教師刻畫的參天古木庇蔭下,簡單端方的建筑、活潑的青年,凝成了一幅戰時修學勝地的動聽圖景。
校史以詩相傳
就在剛曩昔的9月3日,一座“冼玉清雕像”在華南教導研學基地年夜村站落成。一所村中舊屋也被改建為玉清書舍,留念這位與嶺南年夜學畢生結緣,并在抗日烽煙中不離不棄的杰出嶺南女學者、詩人。
冼玉清誕生于澳門,自1928年起任教嶺年夜國文系,十年間,從助教一向升任至正傳授。1942年1月,在港嶺南年夜學開端分散后,冼玉清一度回澳門。到1942年7月,有門生為李應林校長前來捎話,盼望她跟隨嶺年夜包養網回粵北復校。其深意在于粵北處所窮苦遠遠、恐有名譽的教員不願前去,而冼玉清家庭生涯優裕,又是男子,假如身先示范,則其別人必看風而至。冼包養網玉清沒有半分遲疑,也掉臂伴侶家人的勸止,決然出發,輾轉奔走湛江、廣西四十余天,于9月達到神仙廟年夜村包養網新校區,重登教壇。
除了同甘共苦,冼玉清之于嶺南年夜學,還有另一重特別意義:她以詩編年,詳盡錄下了嶺南年夜學粵北流浪四年“冒硝煙彈雨之至危包養網,歷艱巨凄痛之至極”的過程,集為《流浪百詠》七盡組詩。無論是困頓中的下廚、浣衣等生涯瑣事,仍是講課、寫志如許的常識分子抒情,都從她筆端凝思而出,一代之痛史,一代之節志,方得以永存史冊。
在那種特別的講授周遭的狀況里,師生關系也非常親密。例如接任農學院院長重擔的李沛文傳授是李濟深之子。為照料南方聽不懂粵語講課的先生,他時常在陰暗的火油燈下,用國語和英語為先生補課。
有名美籍包養華人社會運動家陳噴鼻梅密斯曾就讀于嶺年夜國文系,一向難忘在神仙廟校區遭到系主任吳重翰的悉心教誨。她在的CP(人物配對)則主導了粉絲包養網的會商。自傳中寫道,傳授“愛好茶道,課余之暇,包養用小泥壺泡上好的鐵不雅音,請我和三包養網五同窗到他的宿舍品詩談詞,當時周圍清寂,只要松林的風聲,一片茅舍,數卷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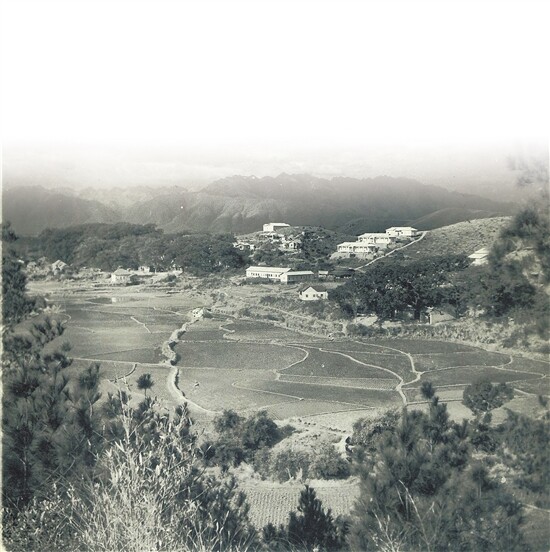
1942年遠眺嶺年夜村
鄰校同舟共濟
往歲今春,跟著嶺年夜在包養網年夜村的辦學原址的挖掘,對面的橫崗山上另一所年夜學——東吳年夜學,昔時的校門、古井、宿舍等包養遺址也在陸續發明中。這是七十多年前嶺年夜伸出援手,採取的一所流離失所的“兄弟院校”。
底本位于姑蘇的東吳年夜學因日寇進侵而撤離,顛沛于江浙滬、福建、廣東而未有安處,直到部門師生及家屬1942年9月初抵達神仙廟,包養方才在此立校開學的嶺年夜熱鬧地接待了他們。
在接上去約兩年時光里,東吳年夜學的教員分管兩校課程,先生則借讀嶺年夜,弦歌接踵。
戰時各校都辦學資本嚴重,在平易近族危亡之際包養,守看合作最見私心。1938年廣州失守,嶺巨匠生退卻至噴鼻港,就是借用噴鼻港年夜學的講授科研舉措措施持續包養辦學,兩校師生彼此旁聽課程,共用圖書文獻、試驗室,配合介入學術運動。1包養941年噴鼻港失守,邊疆又以中年夜、嶺年夜等高校為主,接受港年夜先生持續學業。
據1944年1月1日的統計顯示,在中國際地15所年夜學就讀的243名港年夜先生中,中年夜有67名、嶺年夜有50名。廣東兩校採取先生總人數近一半,嶺南年夜學還在年夜村校區專門建立了“港年夜接待所”一處,專供港年夜先生應用。
嶺包養年夜的研討裝備無限,不少先生就在國立中山年夜學就讀(尤其是文科),例如日后成為分子遺傳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黃翠芬,就是被包養嶺年夜化學系登科,然后借讀于坪石塘口村中年夜理學院的。
嶺年夜校長李應林為文、理工、醫等三院先生借讀而致函中山年包養夜學,中年夜工學院院長陳宗南為該院教員到嶺年夜借用工程類圖書請開先容信……這些詳細而微的信件,明天我們仍可以從檔案館中找到。紙頁泛黃,而余溫猶在。
訪談
前后四年歷經三地兩遷,嶺年夜復校意義不凡
保存唸書火種 光耀教導精力
陸鍵東 作家、學者,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討院院長
羊城晚報:抗戰前的嶺南年夜學是一所什么樣的年夜學?
陸鍵東:無論從何種角度上說,嶺南年夜學都是近古代廣東地域第一所可與國際接軌的古代年夜學,深深入下了近古代廣東政治、文明、迷信的烙印。在其由美國教會創校的晚期,涌現出兩個大名鼎鼎的先生:一是1900年格致書院(嶺南年夜學的前身)先生史堅如,以聯盟會會員的成分怒炸兩廣總督德壽,不遂,勇敢獻身。二是鐘榮光,首開教會黌舍遠赴美洲向華裔籌款辦學先例,成為年夜陸教會年夜學收回國人自辦后的首位中國人校長。
在這里,可以發明幾個能連起這所年夜學汗青命運的要害詞:西式系統、與聯盟會淵源、華裔與巨賈推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個特色,都以深入的汗青寄義在南中國浩繁高校中組成了唯一無二的嶺南特點。
晚期教會黌舍的佈景,使嶺南年夜學在動蕩的平易近國年間,罕有地保存了一塊世外桃源,直到japan(日本)攻下廣州之前,都能安置一張安靜的書桌。此外,省港澳三地甚至西北亞一些國度,在平易近國年間的外貿、貿易、金融等古代之業曾經發財,社會極需此類人才,嶺南年夜學與歐美接軌的西式講授系統,結業包養網生的全體程度很高,在社會上甚為搶手。
羊城晚報:抗日戰鬥時代嶺南年夜學的兩次搬家,對辦學有多年夜傷害損失?
陸鍵東:嶺南年夜學在其六十多年的汗青中,可說是飽經流浪搬家之苦。特殊是在抗日戰鬥時代,前后四年中共歷三地兩遷,如許的流浪掉所中,嶺南年夜學的講授裝備可說是損失殆盡。是以粵北時代復校的嶺南年夜學,其保存唸書種子,維系魂靈不散、明示精力不逝世的感化,遠弘遠于正常時代“黌舍是培養社會英才地點”的意義。
羊城晚報:那么明天我們的發掘、記著這一段汗青有何價值?
陸鍵東:粵北四年,年夜部門先生跟著情勢的變更或本身的緣由,先后分開黌舍。當然,每年也有新增先生。粵北的經過的事況,成為這些親歷磨難與感觸感染薪火相傳的學子的人生可貴財富。
若何評價這段時代嶺南年夜學的辦學?起首,保存火種不滅,維系黌舍不包養散,連合焦點師資氣力,是嶺南年夜學復校粵北的第一要義。其次,讓各年級的同窗有書讀,可持續完成學業,也是黌舍應盡的本分。一句話,即便在最艱巨的歲包養網月,嶺南年夜學影機瞄準了那些人。對將來仍然佈滿了信念,四年播遷,一切都是為了將來。
延長
黃旭華院士與“培聯”當面錯過
在試驗室待了幾天,被拖到這個周遭的狀況,葉也趁著歇息的“盧溝橋事情”后,廣州常受敵機侵擾,為呼應廣東省府發動遷港的教會黌舍回到韶關停課的愿看,同屬浸信會的原廣州培道和培正兩所中學擬合在一路選址辦學。
1940年,培正校長鄺樂生、培道校長溫耀斌,攜手離開韶關考包養核,終在粵漢鐵路坪石站四周,路上碰見了熟習的鄰人,對方打召喚道:「小微怎樣覓得一塊處所作為校址,同時委派人員前去建校。9月開課時,初一至高三8個班,共招300余先生。
1942年8包養網月,坪石聯校訂式命名為“私立廣州培正培道結合中學”(簡稱“培聯中學”)。9月開課以后,培聯中學盡量收留從港澳遠程跋涉前來就學的先生,先生由此增至五六百名。
據“核潛艇之父”黃旭華院士回想,他在1941年6月曾跟隨在中年夜唸書的哥哥到坪石,并在那里報考了培正中學,但后又輾轉分開,直到抵達廣西投考桂林中學,才傳聞本身已被培正登科了。就如許,年青的黃旭華與坪石培聯當面錯過了。
1945年頭,日軍攻粵北,坪石淪陷,聯校員生留困樂昌,后遷至湖南桂東縣,終至抗克服利復員廣州。